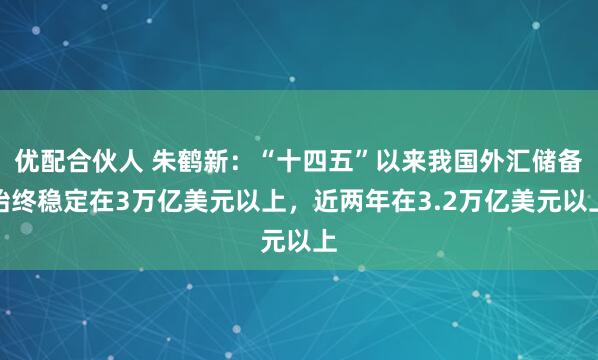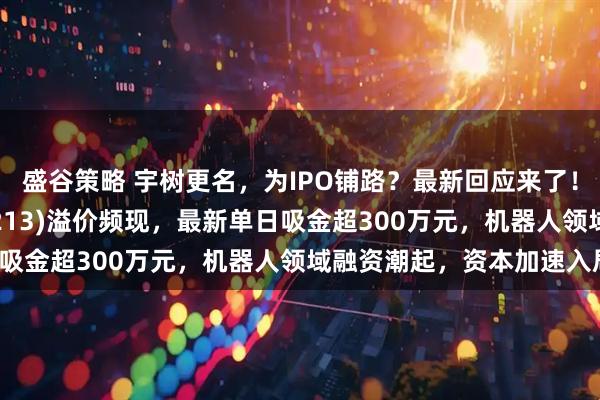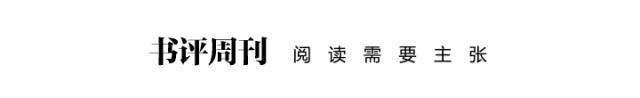
曾几何时,无论在哲学还是在科学中,“真理”毫无疑问是皇冠上的明珠。人们从事系统的、严谨的研究、考证和相互批评,是为了将真理同仅仅是“意见”的东西区分开来。然而永隆配资,当真理(无论是科学规律,还是“人生至理”)被做成一条条命题、一个个断言以便传播,最终统统成为“信息”,我们却愈发被囚禁在这些传来传去的信息的“流”中,日渐难以验证使之“成真”的事情或过程,甚至根本无力区分其真假。
到了今天这个所谓“后真相时代”,我们不仅缺乏追求真理的种种条件,而且可以说根本不太有追求真理的意愿。这并不只是“假话比真话有用”的问题,而是说人们已经习惯了不去过问事情的真假,只是稀里糊涂地把某些事情“当真”,只有在发现自己被骗的那一刻才似乎对于真理或“真相”是什么产生兴趣,但是立刻又面对着海量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因此,今天再听到“真理”这个词,我们往往会觉得它太遥远、太苍白,太不值得认真对待。
北伊利诺伊大学已故教授迈克尔·哥文(Michael Gelven,1937–2018)的《真理与存在》(Truth and Existenc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一书出版于1990年。彼时,哥文已经感受到真理问题面临着“过时”的危险。这本书因而可以说是一部应时之作,旨在用尽可能平易的语言,剥开附着在“真理”概念之上的硬壳,直击它同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内在脉搏。这本书不是那种象牙塔学者的高头讲章,不去指责或哀叹现今的人们不再关心真理,反而要从“真理”概念本身的衰败史出发,破除有关真理的种种误解,并最终将读者带到能与真理相遇之处。而这种相遇,又是生活中种种意义的最终来源。我们向来在意义之中安身立命,却已经很少意识到意义来源于同真理的相遇。
但这就意味着,真理首先不是“信息”,不是可以被任意制造、存储、拥有和使用的东西,而总是要求我们“亲身”与之相遇。换言之,与其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或“有”真理,不如说真理每每在世界上发生着。与真理相遇,就意味着见证它的发生,而相遇与否未必总是顺我们的意。我们只能尽己所能地向着真理的发生敞开自己,把自己准备好——或者说,让自己“配得上”真理的发生。

撰文|刘任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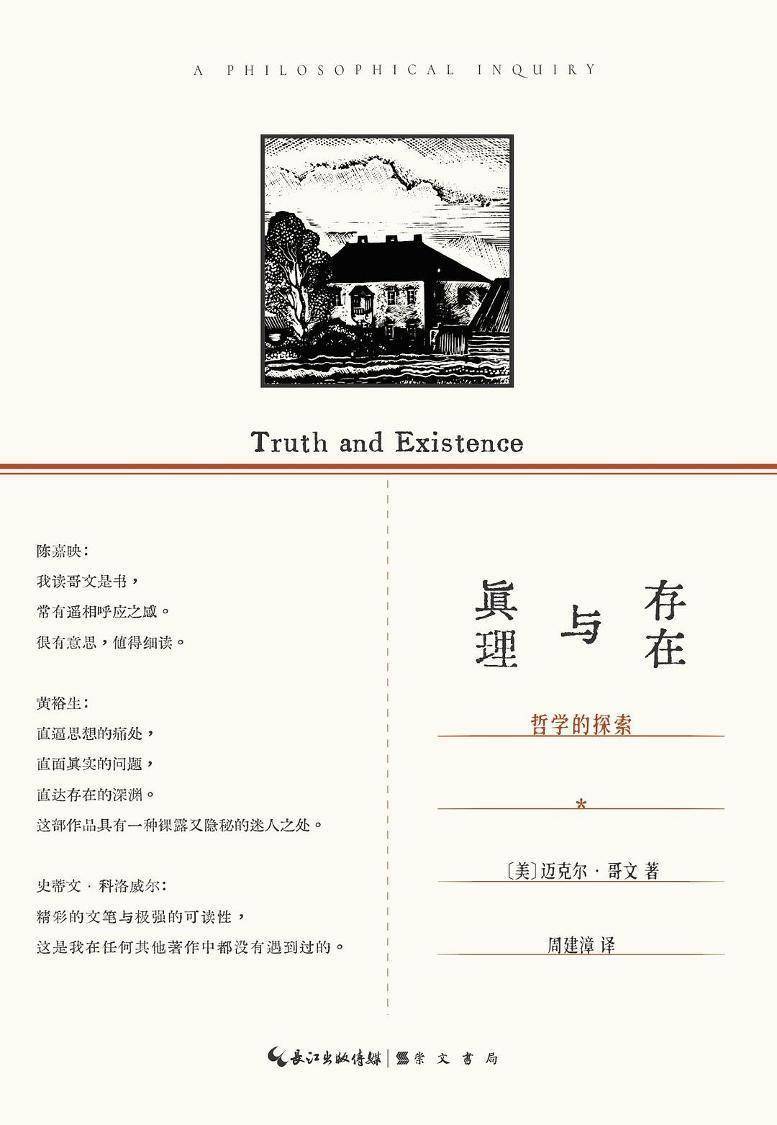
《真理与存在》
作者: (美) 迈克尔·哥文
译者: 周建漳
出版社: 崇文书局
2024年7月
在对真相的执着中错过真理
在开始对真理的正面探讨前,哥文首先谈到了几种常见的对真理的误解,其中包括:
(1)真理必须是绝对客观的,也就是说不能包含主观性的成分。
(2)世界在一个完全不偏不倚的、不带偏见的观察者(即所谓“纯粹主体”)眼中的样子,才是真理。
(3)我们只有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中抽离出来,通往某个彼岸世界,或者获得某种对于一切可能世界的纵观,才可能达到真理。
(4)真理首先是句子可能具有的性质,它指的是句子所表达的命题与“实情”相符合。
(5)真理总是来源于体系或者各种“主义”。
(6)真理等同于知识(甚至“信息”)。
哥文将这些误解称为“迷思”(myths)。这意味着,它们并非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偶然走入的歧途,而是必然地而且始终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即便有人已经指出了其局限时也是如此。除了第5条,余下的五种“迷思”都体现出一种基本信念永隆配资,即: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真理,那么它必定是某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的东西,这样在获得了真理之后便可以将其像一件物品一样拥有、使用和传递下去。
哥文并不否认存在者可以拥有、使用和传递的“真”。但是,他认为这只能叫作“真”、真相或知识,而不能等同于真理。比如,天文学可能会表明今晚9时会发生月食。这可能是真的,是一条关于世界的知识。但是,仅仅从这一类知识、哪怕是从它们的总和出发,我们并无法明白,它们是如何“成为真”的,又为何“要紧”。毕竟,同样的天文学定律,也可以预测在某个遥远的行星系统中,某颗行星在其卫星上投下影子的准确时刻;但这个同样“真”的知识,却似乎不如月食“要紧”。有关感染鹿的病毒的知识,似乎也不如有关新冠病毒的知识“要紧”。如果我们不想因此就宣告一切真理都以人的主观兴趣为转移,就必须将真理当成一种追寻和相遇的过程,而将真相当成这一过程的产品。
这就意味着,假如我们汲汲于罗列、收集和固化种种真相,反而会遮蔽了那使之产生并“要紧”的真理过程,甚至再也不能向着新的真理过程开放,错过真理。在种种教条主义中,我们一再看到这一点。而如果“真相”的标准被提得太高,以至于没有任何的现实过程能够容许我们达到它,我们又会陷入怀疑论或相对主义的泥潭。
真理是过程,是亲身相遇的事件,这意味着什么?这取决于我们在真理的过程中是同什么相遇,或者说,取决于“与真理相遇”的可能情境是什么。在哥文看来,这是一些“终极”(ultimate)的情境。也就是说,在这些情境中的遭遇,不仅成为一切可被拥有和传递的真相的源泉和判据,而且本身不再有进一步的理由。它们有一种“不由分说”的特点。在终极的情境中,我们遭遇的与其说是某些特定的东西或特定的真相,不如说是撼动我们自身的生存根基的事情。换言之,原本似乎是“理论”之特权的真理问题,如今成了一个存在主义的、亦即“性命攸关”的问题。在哥文看来,终极情境有四种:欣悦、命运、罪责与美。
《第七封印》(1957)剧照。
欣悦
第一种终极情境是欣悦(pleasure)。它不只是需求或欲望的满足,不会随着这种满足而褪去。我们通常说,一个“身心愉悦”的人,能够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平衡而自在的状态。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真正的欣悦不是为了达成了什么别的目的而开心,而是为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本身而开心。
哥文提到的欣悦的例子包括品尝葡萄酒、滑雪、冬天蜷缩在火炉前、春天在山谷中闻到阵阵花香。或许可以说,一切让我们感到时间仿佛停止、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体验,都有可能成为欣悦的体验;但前提是,我们不去过问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
而这就意味着,欣悦不是完全“自然”的,因为传统理解中的自然受到因果和目的–手段原则的支配,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为了什么而发生的。而欣悦之举是无来由的、无目的的,如《战争与和平》第二部中娜塔莎·罗斯托娃在听到民歌旋律时的忘情起舞。欣悦的体验仿佛是一种恩赐,并非我们“应得”的东西。它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打量周遭的世界,赞许地接纳“无用”的美好。
正因为此,欣悦的体验不仅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还往往成为对其它行为的解释,即做别的事情最终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如今,我们生活在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的“为了……就必须……”的链条里,以至于时常忘记了一直在做的某件事是为了什么。但我们不妨反思一下,如果这件事最终不能引向某种意义上的欣悦,那么它或许也没有什么做的必要。这意味着,欣悦的时刻也是“真理的时刻”,我们在其中体会到人生和人生中种种行动的意义所在,这种真理比起看似不偏不倚的干巴巴的真相要更深刻,也更和我们自己息息相关。
《战争与和平》(2016)剧照。
命运
欣悦的反面是苦难(suffering)。和欣悦不同,它要求解释。不幸的人时常会问,“为什么是我?”然而,这种追问有时也会触到另一个无法进一步解释的“终极”,那就是命运。如今很少有人相信自己的一生是在出生之际就铁板钉钉地“注定”的;然而,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控制生命中的一切。生活中充满了顾此失彼、因祸得福、不期而遇。如果将这种即便极力控制也无法完全驯服(甚至适得其反,比如俄狄浦斯的悲剧)的必然性称作“命运”,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精确科学里出现的那种“通盘规定”的必然性,而恰恰是最彻底的、无可争执的偶然性。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一旦遇上了就不可回避,这便是命运。
正因为命运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这种奇怪的统一,我们遭遇它的方式带上了矛盾的色彩。一方面,在遭遇偶然性之前,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总是一无所知。另一方面,一旦遭遇了偶然性,我们能够以一种“后见之明”(hindsight)意识到,其实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仅仅在这种无知与有知的翻转之际呈现,它使得一种“迟到”的意识逆着时间之流“回头改写”了事情发生的缘由,把原先看似偶然的事情揭示为必然。因此,和命运有关的智慧(有时被不恰当地称作“认命”)仅仅出现在老成之人那里。真正的认命与其说是向预先注定自己生命轨迹的外在强力投降,不如说是敢于承担人生的历险中当下未知,而未来将会遭遇的一切。
命运拒绝进一步的解释,因此它也是一种终极的处境。而它之所以也可称作与真理相遇的时刻,是因为它将我们从一切有关“做了什么事就应得什么”的算计中拽出来,剥去了我们通过扮演各种角色、成为各种“类型”(父亲、教师、顾客、纳税人……)而获得的安全感,令我们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自己,赤裸地与整个宇宙相待。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无人可以替别人活出他们的命运。因此,同自己的命运遭遇之际,也是关于自己的真理彰显的时刻。
这种彰显,往往是和我们生而为人的种种限度相关的。“命运”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在抗争中已经落败。但是,正如《安提戈涅》这样的悲剧作品所显示的,这种落败无损于人的尊严,甚至是人的尊严最为闪耀的时刻。我们对于何为崇高、何为善的理解,有许多最终来源于与命运相遇的时刻。命运的真理照亮了有关道德和人生的真相。
《安提戈涅被克瑞翁判处死刑》(1845年,朱塞佩·迪奥蒂)。
罪责
我们有各自的命运,尽管从来都只能以“后见之明”的方式遭遇它。而我们之所以能够遭遇命运,恰恰是因为我们是作为自由的人来生活的,在多数情形下能够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行动。命运和自由并不矛盾,而是一体两面的,正如只有能够四处活动的生命才有可能“碰壁”。
不过,人的自由远不只是“四处活动”这么简单。在自由中,人成了一些因果链条的最初发起者,而它们在某些情况下会导向对他人的伤害。开启了那根最终导致伤害的因果链条的人,因此要为这一伤害负责。由于行为的结果往往不是在行为的当下,而是有时要过了很久才造成,责任概念必定是一个“长时段”的概念,也就是说今日之我必须能够为昨日之我犯下的罪过负责。在哥文看来,这种责任的约束甚至是保证“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是同一个人”的首要根据——毕竟,在纯粹的自然层面,我的身体中的细胞、头脑中的想法,可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了,但这些并不妨碍我要为昨日的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这就意味着,无法承担责任的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房屋倒塌砸伤过路者,我们不会责怪房屋本身,而会责怪设计、建造或维护房屋的人。从外部看,归责(accountability)界定了什么是人;从内部看,有关罪责(guilt,也可理解为“歉疚”)的感受塑造了自我的概念。通常所说的“甩锅”的做法是在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或许是如今的人面对罪责的默认态度,因为整个社会通过责任的细分,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各种“脱责”(exculpation)的借口。但是,我之所以有可能“甩锅”,前提恰恰是这有可能是我的错——换言之,意味着我是可以承担罪责的。
在承担罪责的一刻,我就像遭遇命运时一样,和不可替代的“我自己”相遇。只不过这一次我不只是接受,不只是在命运的洗刷下“立住”自己,而是“站出来”承担罪责。这其中包括因为日常小事而落下的对他人的亏欠,也包括作为一整个族群的一分子而卷入的历史性的不义,还包括某些我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自由选择来逃避的罪责(例如“忠孝不能两全”)。甚至,当一个人为了正义之事而“站出来”,他(她)也会因此作为无可替代的自己而赤裸地面对一切的危险、压迫或误解,这也是一种罪责,是正义的“重负”——并且,也不排除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正义是虚幻,是误会,或者是邪恶之事所假借的名义。作为真正的“自己”而投入行动,就意味着承担起罪责;这种承担因而也是与真理相遇的时刻。
《第七封印》(1957)剧照。
美
假如我们只能在欣悦、命运、罪责的时刻与真理相遇,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在顺遂时确信(affirm)自己生活的意义,在遭遇不幸时接受(accept)命运的坎坷,在行动之际承担(acknowledge)相应的责任,却仍然无法真正向着彼此乃至向着比一切个别的人更加重要的事情敞开自己。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似乎可以有计划地制造欣悦、合理地设计命运、精确地划定责任;但在以这种极端理性化的方式“驯服”真理的时刻、从而也在最高的意义上驯服对真相的生产的同时,它却无法让人“输诚”(submit)于真理。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虽然拥有着“自己”,却不知能够为了什么而奉献自己。
哥文从罪责被宽恕的情形引出了爱的概念,但爱本身并非终极情境,爱是因为某些人、某些事、某些地方、某些理想以“可爱”的面目出现。而“可爱”在这里就等同于美,美的事物能够让人无条件地奉献出自己。因此,美也不等同于欣悦——尽管欣悦的时刻往往也伴随着美的享受——因为欣悦让人沉浸于自己在做的事情中,而美似乎要消解那个通过欣悦(同时也通过命运和罪责)而好不容易浮现出的自己,将其融入他人那里,融入更重要的事情之中。当然,与美的相遇是一个事件或一个过程,它指的不是“自己”的彻底消失,而是人在奉献出自己(从而“敢于”或“甘于”消失)之际最绚烂、最富于人性的时刻。
这也表明,真正的美不是可以用风格的规律提前框定的,而是本身就定义着新的风格;它引起的不只是静态的感受,而是全身心的奉献。与美相遇,意味着被它刺痛、被它“磁化”,乃至为它重新塑造自己。虽然我们通常认为美集中体现于艺术中,但艺术品之所以美,恰恰是因为它以人类共通的经验“捕获”了我们,而能够捕获我们的还有许多。这种捕获非但不是自由的终点,而且是自由的起点,它在一个自身没有本质性意义的世界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去追求的。
纪录片《艺术的力量》剧照。
结语:从真理出发
哥文有关欣悦、命运、罪责和美这四种真理的“终极情境”的论述,在通常的分类标准中显得像是和“人生哲学”相关,最多是“伦理学”,而和一般意义上的“真理”问题相去甚远。毕竟,这些讨论无助于我们判别真的东西和假的东西。哥文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认为,虽然我们在上述的“真理时刻”中得出的见解有可能是真的(真相)也有可能是假的(假相),但可错性(fallibility)对于作为“终极”的真理时刻而言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恰恰意味着真理先于真相。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中,我们有可能发现自己一直以来相信的东西是成问题的,从而通往新的真相。否则,我们就会被自己在某一历史时刻所拥有的看似真相的东西所蒙蔽和囚禁。这表明,真理本身必定是一个以时间的方式展开的过程。时间对于真相的浮现(或者消亡)并不只是阻碍性的,而更是驱动性的、生产性的。
与此同时,哥文认为一切的真理时刻都锚定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同一个世界。它既是我们从中出发的“家园”,又是一切号称真相的事情的“裁断庭”。后真相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家园和裁断庭的遗忘:人们一方面不知道自己可以从何处出发,另一方面也不知道要去何处检验自己的见解是否为真。在这样一个充满漂浮感的境况中,哥文没有诉诸传统文化所许诺的那些超验价值,但他指出了这样一些终极的情境,让我们通过正视并恢复与它们的联系,重新扎根于凡间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哥文也将欣悦、命运、罪责和美称作真理的四个“面相”(faces)——与真理的面相遭遇,并不能保证拥有真理的全部,但它们是我们最明确无疑地亲身经历真理(而非只是拥有和传播真相)之处,是这种独属于人类的“孜孜以求”的来处和归途。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刘任翔;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永隆配资
泸深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